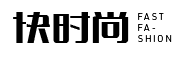现代恋人的自由:重读弗洛姆和沙特
导读:弗洛姆(Erich Fromm)在〈自私与自爱〉(Selfishness and Self-Love)里说过:「爱不能分离於自由和独立爱的基础前设是自由和平等。它的前设是使我们能承受孤单﹑忍受孤独的力量﹑独立性...
弗洛姆(Erich Fromm)在〈自私与自爱〉(Selfishness and Self-Love)里说过:「爱不能分离於自由和独立……爱的基础前设是自由和平等。它的前设是使我们能承受孤单﹑忍受孤独的力量﹑独立性和自我的完整性……爱是一种自发的行为,自发性是指(同时在字面上)按自身意志行动的能力。」

了解弗洛姆的人都知道,他在《逃避自由》(Escape from Freedom)中对「自由」这个概念作出了两种区分:先是「不受其他东西所限的自由」(freedom from);其後是「做一件事的自由」(freedom to)。当中的概念,似是以赛亚.伯林(Isaiah Berlin)对消极自由(negative liberty)和积极自由(positive liberty)的两种区分。
弗洛姆又提到,人会为了不承受孤独而甘心放弃一些消极自由。放在爱情和两人关系的语意下,我们可以很容易想像各种情绪勒索,甚至是家暴的例子。对於那些,这边就先不多说了。我反而关心的是,到了现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,恋人间的自由又成了一个怎样的状态。
从脸书的广告风波看恋人的自由?
在早前脸书的听证会後,在浏览谷歌等网页时多了一项提醒,要你在一些新的私隐条款下按上「同意」一项。在现今的网络世界里,我们已经很难阻止自己的私隐成为广告商的目标。
早期笔者写过一篇名为〈网上社交的现代性:重读鲍曼和巴特〉的文章,讲述现代的某种恋人状态。当中我说过,不知是甚麽原因,脸书总是「按我的需要」为我打了不少社交软件的广告。这不是重点,我想说的是,假如你像我一样单身一人,那脸书给你打甚麽样的广告,大概也不会对你有甚麽大影响——最多就感到有些厌恶。但试想想,如果你已有家室,但脸书或谷歌还给你打社交软件的广告,而你的伴侣又理解到脸书以「投其所好」的方式显示广告,你可能就会招惹血光之灾。
在现今互联网的运作方式下,人的消极自由彷佛受到了一种新的限制。即使,从来没有人明确地为我所浏览的东西划下限制(没有人主动侵犯我的积极自由),但当我知道,自己的伴侣可能会无意中看到媒体给我的广告,我便会开始自我审查,变得小心翼翼。
而且,这种情况可说是无孔不入的,我们甚至可以很轻易地想像,即使只是随意在YouTube看看影片,它就「聪明地」为你推荐你可能想看的东西了。这个时候,恋人的嫉妒情绪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唤起,继而引起纷争。
恋人的嫉妒与自由?
罗兰巴特(Roland Barthes)曾在他的爱情圣典《恋人絮语》(Fragments d'un discours amoureux)说:「嫉妒是在爱中诞生的情感,是由於恐惧所爱的人更喜欢别人而产生的……是一种排他的行为。」当恋人看到媒体为自己恋人所提供的偏好,便产生了某种恐惧,这种恐惧继而成为了试图限制伴侣的动力。
不过,说到恋人的嫉妒和自由,又不得不说沙特(Jean-Paul Sartre)。对於沙特,人作为一种具有意识的「为己存有」(being-for-itself),我们是无可避免地自由的。然而,当他者(the Other)出现,而我们又意识到他者同样是一种为己存有,我们的自由便受限了。
在《存在与虚无》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小节〈注视〉(The Look)里,沙特透过描述偷窥别人的例子,先说明一个人如何意识到他者不只是像「在己存有」(being-in-itself)般的客体。他说,试想像自己是一个从门後的钥匙小孔偷看的人。你因为嫉妒他人,便从小孔窥看别人的一举一动。在开始时,你乐在其中,以为自己完全躲在了无人能发现的黑暗之中,在过程中你不经反思地把别人当成了像「在己存有」般的客体;但当你听到身後的脚步声,发现有人向你走近,把你逮过正着,你的处境也就因此而改变 ── 这刻你知道别人在注意着你。正正是因为这种处境的改变,和你在两种处境下所感受到的感觉迥然不同,沙特便把「为己存有」的特质从个人的层面推展到他者——他者亦具有意识;他者是「在他存有」(being-for-others)。
重要的是,在你由嫉妒转为感到羞愧的过程中,你的自由也同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。这里听在上可能有点矛盾:在一方面,沙特主张我们有无限的自由,又我具有意识开始,我们就被判处(condemned)为超越自身本质的「在己存有」。自由是一种想像能作另一选择的能力,因此我们亦没有停止自由的自由。那麽,他者的出现又如果令我不自由呢?
沙特与西蒙波娃
沙特与西蒙波娃
正是因为「在他存有」的出现,我对自身的察觉也不同了,我的行为可能是我选择的结果,但我知道我的行为同时被他者所描述﹑归类﹑评价,我的自由嬗变为他人的感知,就如沙特说:「他者成了我和我自己之间,不可或缺的中间人。」因此,当沙特一方面说:「我是我的行为」;但在另一方面,我又在两层意义下抽离於自己的行为:首先,我不是我的行为,因为我的自由不在於我所选择做的事,而是在於我在可能选择做其他事的能力。其次,我不是我的行为,因为我无法控管他者如何去看待我,而这个「我」会因他者的感知方式受到改变 ── 他者可能对我有好的评价,那我就是好的;反之亦然。
也就是说,在严格的意义下,他者并不是直接的限制了我的自由,而是透个改变「我」而使得我不自由。亦正因为如此,嫉妒成了构成「我」的存在状态,而羞愧则把我从「我」中抽走(沙特说,这想法是受到黑格尔的启发)。 而这种意念更是显示了在沙特的文学作品中 ── 例如,在他的剧作《无处可逃》(No Exit)中,三个刚死的人被迫共处一室,他们试图以谎话粉饰过去,最终却又躲不过他者的目光,继而带出「他人就是死狱」这个广为人知的主旨。
现代恋人的自由?
根据沙特,嫉妒的偷窥者是自由的。按照沙特的思路,被偷窥者只要不知道自己被偷窥,他应该也是自由的。但如之前所说,在现今的世界,一个人难以在走过的路上不留下痕迹。更甚的是,在现今的世界,就连「我」这个概念也彷佛能化约成数据,被一个新的方式重新再定义。因此,恋人不止没有某种消极自由;当对方无意中看到自己的电脑中的广告﹑或是影音网站的影视推荐,恋人的「我」也随即被凝视,继而不再自由。
更甚的是,在现今世界,恋人总是无时无刻感受到自己可能被「偷窥」。在现今互联网通讯的社交方式下,恋人几乎是「无所不在」的。在从前,恋人收到了对方的一个来电,他可能假装不在家;在不远的从前,恋人的手机响起,他可能假装睡了;现在,恋人只要曾经上线,他的行踪就被记录下了,他无法逃避了。恋人是不自由的。恋人收到对方的一个讯息,他在回覆与不回覆之间徘徊,他不小心打开了对方的讯息,他便不再自由。
但是,我们有选择放弃自我﹑放弃自由的理由吗?弗洛姆曾在他的《爱的艺术》(The Art of Loving)中探讨过「自爱」这个概念。自爱很像就等於是爱己和自利,彷佛跟爱别人是相矛盾﹑相对立的,但经过细心的思考,弗洛姆反而认为爱别人和爱自己是不可分的。
首先,自利的人其实并不爱自己,试想像一下,一个嫉妒的偷窥者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?他担心对方会对自由做出不忠的事,在一方面他是把对方视作自由利益的一部分,而非一个独立的主体。嫉妒的偷窥者虽然从嫉妒中获得了自主性,但一个懂得自爱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就不会嫉妒。这便连系到弗洛姆的第二个观点。一个嫉妒的偷窥者之所以不懂爱对方,其实源於不懂自爱。假如嫉妒构成了偷窥的恋人的自由,那麽他可能真的有放弃自由﹑放弃自我的理由。
不过,沙特显然不会同意弗洛姆的观点。沙特认为恋人的关系更像是权力的角力,他甚至认为以社会道德规范去证立自己的行为(例如:弗洛姆所说圣经中的爱人如己),本身就是一种「坏信仰」。「坏信仰」是一种对自己欺骗,同时是对别人的假装,假装自己没有自由。换句话说,与其说所谓的道德人生是一项成就,倒不如说它是对自由的逃避。
但更重要的是,即使沙特认为恋人的自由迫於无奈地被恋爱对象所限,我们还是不得不去爱,因此,沙特的解决方案是:既然「我」是被恋爱对象定义的,我就只有透过成为对方来从新获的「自己」。因此,在表面的层面看来,沙特和弗洛姆两人的主张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分别,他们都很像消除了爱人和爱己的区分,继而消除了「我」和「他者」的区分。
此稿件为延展阅读内容,时尚生活网不对本稿件内容真实性负责。如发现政治性、事实性、技术性差错和版权方面的问题及不良信息,请及时与我们联系
分享: